【追思】
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
考古学家、考古学教育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宿白,因病于2018年2月1日6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宿白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科的主要创始人,是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是杰出的考古学教育家。他领导创办了北京大学的考古学专业,规划了中国考古学科的教学体系,在北大任教逾七十载,为新中国的文物考古事业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正是鉴于他的杰出贡献,2016年5月,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授予其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将在北京大学红五楼5101室设立灵堂,2月2日—5日接受吊唁,开放时间为每天10时—17时。2月5日10时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宿白2013年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摄/光明图片
光明日报北京2月1日电(记者李韵)早上打开朋友圈,心立刻就沉了下去——宿白先生清晨驾鹤西去了。考古文博界的群里,“宿白先生千古”瞬间刷屏。
宿白,中国考古界当之无愧的泰斗,当今业内诸多“主心骨”级的人物都是他的学生。记者拨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家瑶的电话。“我一早得到消息赶过去,在太平间见了他最后一面,陪他待了半个小时。”电话那边,带着颤音。“尽管有准备,可还是觉得他走得太快了。前天晚上我还到医院去看他,他的手还是热乎乎的。”安家瑶极力控制着情绪,“他一直催我‘你回去吧,回去吧’。没想到这竟是先生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作为宿白的得意女弟子,安家瑶说,在她眼里,宿先生不仅是位严师,而且是一位长辈。“今天陪先生的那半个小时,往事不断浮现在眼前,历历在目,就像昨天一样。”她刚上研究生的时候,先生带着学生在武汉实习,一起住在武汉博物馆的旧招待所里。每天早上先生都会去叫学生起床跑步,跑到东湖再折回来。宿先生一直认为,身体好是工作好的前提。“先生自己掏了20块钱,让我们去买螃蟹,还教我们怎么吃。”安家瑶沉浸在回忆中。
“前些日子,国家文物局通知今天要开个迎春茶话会。我跟先生说,文博界的那两位老人肯定会去,您也去吧。今天,96岁的谢辰生和96岁的耿宝昌先生都去了,可是96岁的先生却走了。”安家瑶哽咽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导严文明先生也参加了今天的茶话会。他说,茶话会开始前,与会的文博界人士全体起立为宿白先生默哀,因为“宿先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严文明既是宿白的学生,也曾在宿先生任北大考古系主任时担任他的副手。他说,宿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但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他不允许自己出错”。1959年,宿白去西藏进行文物调查,行前查阅了大量藏传佛教的佛经。进藏后,每到一处寺庙,他都要认真测量,缺少工具,他就用步测,然后做了非常细致的记录,画了图。“文革”期间,大量寺庙被毁,而根据宿白的笔记,居然可以很好地复原出来,足见笔记的精准性。
除了严格,宿白的勤奋也让严文明记忆深刻。第一次去美国,一个多月时间,宿白把所有空余时间都泡在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查阅那里的善本书,而且做笔记。一个多月,16开的笔记本,厚厚两大本,“密密麻麻,而且字迹非常认真,像印刷的一般。”严文明说。类似的事情,在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又再现了。正是这种勤奋,使得宿白的学术视野很宽。他不但教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的考古,还可以教古代绘画史、古代建筑、版本学、目录学。而佛教石窟寺考古的第一把交椅,迄今无人能接替他坐上去。
与严文明和安家瑶两位已过花甲的专家相比,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的博导李梅田和韩建业算是当今考古界的中生代了。作为学生,他俩不约而同地认为先生给人最深的印象是严厉与严谨。
“在先生面前,偷不到半点懒,耍不得半点滑,否则会招致严厉批评,以至于每次与他见面汇报学习,都会非常紧张,甚至毕业多年后汇报学业,仍然如此。”李梅田坦言。
他回忆说:“有一年,按他的要求,我整整一个学期都在善本室看《云冈石窟》。临近春节的一天,宿先生来善本室,我跟他说还差3卷没看完,但是要放假了,善本又不能外借。原以为他会让我回家过年,开学后再读,没想到他说,那你春节就别回家了吧,我跟图书馆说说,你把书借到宿舍读吧。就这样,我整个春节都在宿舍读善本。春节前当我拿着两大本笔记向他汇报时,他乐呵呵地说:‘光读还不行,还得思考,写篇文章吧!’又从书架上拿出两本云冈图录,嘱我写一篇作业。于是,我的整个寒假就这样在宿舍里度过。”李梅田坦言:“当时心里是有怨言的,但回想起来,我的学术生涯仍主要得益于硕博7年里高强度的读书经历。”
“宿先生于我,是神一样的存在。他把考古和历史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方式,前无古人,迄今无人超越。”韩建业说,“他要求我们写论文‘无一字无出处’,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至今影响着我。”宿先生讲课前总是准备了非常详细的讲义,但在课堂上并非照本宣科而是娓娓道来,却又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韩建业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宿先生上古代建筑课,在黑板上画各种佛教建筑的图,既快又好,令人叫绝。
宿先生弟子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论文发表前要请宿先生过目,而大多数情况下是会受到批评的。但正是这些悉心指点,才让学生们懂得学术的严肃性。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怡涛,认为宿白先生教给自己最精髓的就是要“做纯粹的学术”。他说:“或许,这个社会不能让我们做纯粹的人,但还是要努力做纯粹的学术。”而这也是他正在努力传递给自己学生的。他给记者举了个例子。曾经有一位博士生,因为论文不合格,迟迟不能毕业。他跟宿先生说,学生也有苦衷,拖家带口读博不容易,毕不了业影响真的很大。但宿先生说,那可以不读呀,绝不能因此降低学术标准。“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先生的话很不近人情,但是后来想,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的确,生活一时的困难,不能成为降低学术水平的理由,否则学术就没有标准了。”很多类似的事,让他认识到,“宿白先生非常可贵的品质就是非常纯净,就是学术,无问其他。”
【记者手记】
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
“没什么特别的”宿白先生
我与宿白先生并无深交,见他,多是在每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上。作为考古界的泰斗,在那种场合,想和他说话的考古人太多了,根本轮不上我开口。于是很多次就那么远远地看着众位考古大咖洗耳聆听他教诲的恭敬样子。
2013年春,“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如期召开,却没有见到宿先生。知情者说,宿先生91岁高龄,身体不太好,这么高强度的工作不敢请他参加了。就在那时,“抢救性”采访的念头在心里长了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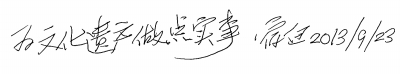
宿白为《光明日报》题词“为文化遗产做点实事”。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摄/光明图片
电话打到家里,宿先生开始一直婉拒,“我那些做的事儿,没什么特别的”,总让我去采访其他学者。从7月开始,我隔段时间就打个电话,“死缠烂打”的战术终于奏效,他同意给我两个小时。
9月,一场秋雨让京城的气温骤降。绵绵细雨中,我如约按响了宿先生家的门铃。
不大的房间,老式沙发,木头桌子,柜子里、桌面上、沿墙边都堆放着大量书籍,这也和许多学界大家一样,一切就如宿先生的口头禅所说——“没什么特别的”。
虽然之前有过多次电话沟通,但说起考古生涯,老先生还是连连退缩:“都是些该做的事儿,没什么好采访的啊。”面对记者不依不饶的“纠缠”,宿先生笑了,开始用略带东北味儿的口音讲起了自己的“想当年”。
田野考古,无疑是辛苦的——“远看像要饭的,近看拣陶片的”,这是人们对考古队员的描述,虽然夸张却也反映出田野考古的艰辛。然而,宿先生却总是说“没什么特别的”。说到1951年冬季在河南白沙水库考古,春节在工地过,他竟然说:“在深埋于地下的墓穴中竟也未觉寒冷。当时大家的热情很高,很专注,也就不觉得冷了。”说到1959年和1988年两次入藏做西藏地区首次文物调查,路途劳顿、高原反应,都被他轻描淡写地带过,而说起调查到的文物情况却是滔滔不绝。其实,明白人都知道,当年田野考古的条件比现在艰苦多了。
聊到取得的成就,宿先生的口头禅“没什么特别的”出现的频率就更高了。谦虚,在宿先生那里,不是形容词,而是化入血液、如同呼吸般自然。
采访结束前,我请宿先生为《光明日报》题个词。他略为思索,写道:“为文化遗产做点实事。”“咱们共勉吧。”他说。
《光明日报》( 2018年02月02日 09版)
- 上一条:张卫明“人民是阅卷人”的价值意蕴
- 下一条:检察机关应是“错案追究的第一责任人”



















